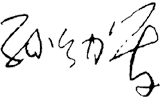|
|
||||
前言与代序
|
||||
|
孙幼军 |
||||
|
|
|
|||
|
我最早接触到书籍是三四岁的时候。那时我家住在哈尔滨,爸爸是铁路局的一个小职员。他精通俄语,而且正在日本研修“铁道”,有条件给我弄来一些外文的幼儿读物。这些书的文字是方块儿的,还是弯弯曲曲的,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反正我一个大字不识,全靠爸爸讲给我听。此外,那些大本本里满是图画——一只穿衣服、戴帽子的猫开着一辆敞篷汽车,显得非常神气;水里漂着一个大桃子,大桃子切开了,里头跳出个小娃娃……光是这些图画就把我迷住了。隔着一道绿栅栏是另外一家铁路员工的小院子,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女孩子,总隔着绿栅栏和我说话。她举起她的玩具给我看,我也向她举起我的图画书。她后来终于绕道跑进我家院子找我玩儿,肯定同这些漂亮的书有关系。我至今还记得她把两手放到背后,贪馋地盯着我那些书的样子:“我看看行吗?”这使我感到无比骄傲。看来当时能拥有这种宝贝的孩子是很少的。 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爱上了书。 我自己买书是从全家来到流亡关内的第二站“北平”时开始的。我家住在北锣鼓巷纱络胡同15 号,离热闹的鼓楼大街很近。爸爸失业,日子是很艰难的。但不论怎么穷,孩子总是家庭里最少受委屈的成员,尤其我这个长子。早晨上学,我总有几分钱的早点费,逢年过节,还有些额外收入。那时我迷恋上了武侠小说,早晨买“油炸鬼”的钱都被积攒下来,送进鼓楼大街书摊儿小贩子的腰包。过年时拿到“压岁钱”,我更是乐得发疯,一连好几天在马路边转来转去。路边的店铺和摊子上,许许多多的美味食品散发出诱人的光芒,但是书摊儿和小书铺才是我心目中藏着蜜糖的鲜花,我这只贪婪的小蜜蜂只是从这一丛花飞向另外一丛,对别的全然不顾。《十二金钱缥》。《女侠黑龙姑》、《七侠五义》、《牧野雄风》、《侠义英雄谱》……我很快就拥有了一大批武侠小说。记得当时我最喜欢的是一套《济公传》,我一边读一边笑,反反复复,也不知看了多少遍。四十多年后我写了一部叫《仙篮奇剑》的长篇传奇,有人称书里的主人公为“小济颠”,使我深感童年读书影响之大。我还买过一本叫《琥珀连环》的武侠小说,里边写了三个少年的恩恩怨怨,其中两个主要人物葛天翔和王天朋有比较鲜明的个性。1945 年我就同这本书分手了,以后再没见过,居然半个世纪之后,他们还鲜明地留在我脑海里。在我已老得连相处二十多年的同事的姓名也会一时叫不出的情况下,仍记着“王天朋”也实在是令人感到惊异的事。 日本投降以后,我全家回到东北,在长春安营扎寨。我进入了自己童年读过的第九所小学,没有改变的是对课外书的浓厚兴趣。像搬到别的城市一样,我对新环境最先熟悉的是旧书店和小书摊子,不管它们多么远、多么隐蔽。二马路“爱文书店”那位秃顶老板笑嘻嘻的面容至今恍如在眼前。他容忍我长时间一册册翻阅他的书,态度相当友善。只有一次他很神秘地把一叠画着光屁股小人儿的画片拿给一个顾客看,我也好奇地凑上去时,他向我板起了面孔。还有一家叫“文叶书林”的旧书店,也是被我踏破门槛的地方。 妈妈给我的零花钱比以前多些了,但我买书主要还是依靠节省下的饭钱。中山区国民小学离开我家并不太远,由于我二弟幼忱双腿有残废,我俩往返不易,午间那顿饭经常在学校附近的食品小摊子上买。为节省下钱买书,我总买最廉价的,甚至干脆饿肚子。开始对书籍产生兴趣的二弟幼忱不久也仿效我,为我的图书积攒工作“投资”。在他成为作家之后,常在文章中回忆这一情景。 钱少又促使我开辟了一个很特别的图书来源。学校附近有一条颇类集市的小街,我在那里发现了几个论斤出售旧书报的小摊子。那年月缺乏包装纸,一些卖杂物和小食品(如花生米、瓜子)的店铺主要用旧报纸包装零售商品,这些旧书报小摊子也就应运而生。包装用纸以大张的为贵重,最受欢迎的自然是报纸,其次是杂志,末等的是“书本本儿”。但是对于我来说,情况刚好相反:最贵重的是书本。在那些书本里找到文学作品,尤其是我想要的文学作品,近乎沙里淘金,我却耐心十足,不断去那里寻觅。书本都用绳子捆着,只有一侧露出书脊,书脊朝里的更判断不出是什么书。我蹲在那里发掘,很招小贩子嫌恶,他们总是呵叱: “走,走!别处玩儿去!” 我小心地回答,我不是“玩儿”,是想找几本书。他们仍不耐烦地说: “不够两斤不卖!” 我的办法是掏出钱来给他们看,还说:“贵一点儿也行!” 这一招儿很奏效,他们终于肯解开绳子,让我挑选。我选得多时,他们也上秤去称,价钱比报纸还要高些;书少时他们就用手掂掂,随口说个价儿。不论是哪种情况,这儿的书都比书店便宜得多。除此之外,有许多书是书铺、书摊儿上根本找不到的。我的大部分儿童读物如《爱的教育》、《闵豪生奇游记》、《稻草人》、《两林的故事》、《秃秃大王》、《寄小读者》、《鲁滨逊漂流记》、《木偶游海记》、《古代英雄的石像》等等,都是这样买来的。幼忱在他的自传体小说《通向奇异世界的小路》里有一段描写:
爸爸每天早上,把买午饭的钱交给哥哥。每天中午,我只要在教室里等着就行了,哥哥到时候,会把温热的油条呀,馒头呀,烧饼呀什么的,送到我手边。一天中午,我肚子饿得咕咕叫,哥哥却迟迟不来。等我见他喜气洋洋地来到我身边时,就断定他一定买了什么好吃的。不料,他递到我面前的,仍是一个馒头。 ……他掏出一样东西在我眼前一晃。我马上就成了个泄气的皮球:什么宝贝啊,折腾了半天,原来不过是一本书,而且,书还是旧的。 他见我失望的样子,就把书摆在我面前,让我看书的封皮。我念道:“木……”哥哥指着第二个字告诉我,这个字念“偶”……,于是我又从头念道:“木、偶、奇、遇、记。”
虽然幼忱写的是小说,这一段描写却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书越积攒越多,放得到处都是。在纷纷回国的日本人把家庭里的东西摆满大街出卖时,爸爸曾买了许多日文书籍,光是一套《世界文学大系》就有厚厚的几十卷。为摆放这些书,爸爸还同时买了些书架、书柜。看到我那么些书,爸爸腾出个带玻璃拉门的小书柜给了我。我把“藏书”都装进小书柜,一时兴奋异常,寻个木块,自己用铅笔刀刻了“小小图书馆”五个四四方方的阳文字,在幼忱的协助下,把每本书都盖上大印。我觉得自己已经当上了图书馆的馆长,并且自信长春城里没有任何一家书店有我这样丰富的儿童文学藏书。 到了六年级,我的阅读兴趣已经从武侠小说、儿童读物转向“新文艺”。1947 年5月23日,我的日记里有这样一项记载:
晚上到文叶书林去租了一本《冰心小说集》,押金是200 元,阅读费(按)20%计算,这还是老主顾的好面子呢!
当时这家书店主要出租的书籍是武侠、言情、历史演义之类,我却去租《冰心小说集》,可见我对武侠小说已不那么热衷了。四日更记有:
我走到书摊的地方去,因为现在天正落雨,所以他没摆摊。我垂头丧气的归路上碰到了书摊掌柜的,所以随他到家里。我们的交换成功了,我给他的是八小本:《郭子仪征西》、《郭子仪地穴得宝》、《青龙白虎》、《唐明皇游月宫》、《三盗梅花帐》、《三探聚宝楼》、《血溅武家寨》、《七子八婿大团圆》,所换得的书有《梦柯》、《炉火》、《老舍幽默集》、《春天里的秋天》、《风沙》……为什么换得这许多书呢?因为他注重古本演义等小说,不注重文艺小说。
在那个时代,书很少。我居然又很快地搜罗到一大批“新文艺”作品,包括鲁迅的多种小说集、杂文集,老舍、巴金等十多位作家的作品,胡适之、徐志摩的诗歌……我的“小小图书馆”越来越像样子了。 我常被小朋友问及“你是怎样成了一个作家的”,我谈我的个性、我的经历、我的日记时,也总忘不了告诉他们: “我曾经是一个小书迷呀!”
|
||||
|
|
||||
|
首页 | 网站简介
| 百问百答
|
||||
|
版权声明:本站的版权所有人为
阿甲 和 萝卜探长 |
||||